该如何向你们讲述协和?一个稍不留心便让人不知顿挫的地方。我第一次,第二次,甚至是每一次站在病房里,站在病床旁,都会觉得无所适从,被一种植根于骨髓的无力感打败,那是来自人内心的最原始的不安,是面对同类而无能为力,即使那人此前我从未见过,而且此后也不见得会遇见。一次偶然的窥视,不过说了几句话,彼此问候几声,一起度过了漫长一生的短暂片刻,便犹如那抛进水里的石子,泛起阵阵涟漪,散发至无穷远处,随着暗流不知涌向何处,在那瞬间石子沉入水底,成为那水,那湖,那海,与之连为一体。
当你走进协和,轻叩下一扇扇虚掩着的门,注视着一副副陌生的脸庞,一双双警戒却写满疲惫的眼神,一个又一个看起来似乎丝毫不起波澜的人生,我是说假如他们的人生真的可以平平淡淡、从从容容,该多好?可这“看起来”的背后究竟埋藏了多少家庭的幸福,我们无从知晓。只记得有次从楼梯走上快乐驿站,看到一位约莫四十来岁的男人,坐在台阶上,我打他身旁走过,几乎听不到哭声,只见他不住的抹着泪。我想停下来安慰他,同他讲上几句话,或者随便做点什么,我犹犹豫豫,却还是迈开步子,踏上那一级级台阶。生活的苦水不比疼痛时的眼泪,后者是一种感觉,而前者暗示了一种艰辛。“阮籍猖狂 岂效穷途之哭”,古人尚且如此,何况今人?又有“行至水穷处,坐看云起时”、“宠辱不惊,闲看庭间花开花落;去留无意,漫观天外云卷云舒”,古人何其阔达,似乎早已超脱生活的柴米油盐、摒弃尘世的杂乱纷扰,比起书中诗云的逍遥,生活苟且。但这生活,却让人喜欢的要紧,你用富贵换不来,你用贫贱夺不走,就好像余华《活着》一书中的“富贵”,在几乎失去了一切之后继续的活着,与从前无异,日复一日的生活背后,意义已经超越了生活本身,至于个中滋味,大概只有真正经历了的人能体悟吧!
比起穹顶上阴霾的天空,协和的空气里更透露着一种难以诉诸言语的沉重,每一口的呼气、吸气都得小心翼翼,可即使是这样,有时也会觉得喘不过气来。之前遇到过一位姐姐,第二次遇见她时,几乎是没认出来,她见我有些窘态,便微微地笑着说,“上次你来时,我带了假发”。语毕,又笑了起来,脸颊的酒窝宛若一朵睡莲。坐在病房的母亲,难免伤心与疲惫,神情之中却依然透露着一股坦然,似乎在向旁人说着,“桥归桥,路归路,日子总还是要过的”,不由得让人敬佩。我不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情景,上回敲门进一个病房,刚进去只见病人慌忙的带上假发,细看之下,她的眼角还红肿着,坐在身旁的母亲,愁眉惨目,看起来叫人好不伤心。说来也巧,这次又遇到了那位高中的小妹妹,而今天又正好她出院,我走进病房时,她和家人刚收拾好行李,准备回家。依然记得第一次见到她时,她躺在病床上,无论我们说什么、问什么,她几乎没有一点反应,只有她爸爸在一旁跟我们不住的聊着,我几次三番的想教她开口,结果只换来一两句干巴巴的回应,再后来遇见她,若是合适,便自顾自话的胡乱说些什么,给她讲些所见所闻,问问她是否有喜欢看的书,喜欢听的歌,喜欢做的事,或多或少,总能得到点回应。看到她时,我总忍不住的回忆起十七八岁时的生活,思来想去,记起的也只有百无聊赖的课堂,假期的一点点闲暇和激动,哦,对了,还有那个喜欢的女孩,时光匆匆,青春只剩下些微不足道的回忆,旧时光总会让人伤感,让人感叹自己太早老去。我又常常想着,倘若我是在病床上熬过我的十七八岁,这时的我又将记起些什么?我无法想象那由病房与点滴夹杂成的青春,命运何其残忍,造化何其弄人,后怕中怀有一丝侥幸。比之于经久世事的老者,或者已尝人生滋味的青年,又或初晓人事的少年,孩童何曾懂得什么?我第一次在协和见到小孩子时,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,不敢相信眼前两三岁,五六岁,七八岁,十一二岁的孩子,挂着点滴,在不到两平米的病床上释放自己的顽皮和淘气,不知十几二十年后他们是否还能记起这样一段往事,那时他们又会想些什么?
来协和是为了什么?有次一个病人的家属,问我们这些人是为了什么,我一时语塞,不知该如何回答,人做的每件事,难道都是为了一个什么不成?这“什么”本身难道不可以什么都不是吗?不过是一个闲人,在一个无聊的上午,去了个不知为何的地方,讲了些不知道什么的话,想想也是好笑,却还有几分意思。不过如此。
|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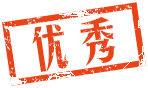
 /1
/1 